发布日期:2025-09-19 20:45 点击次数:165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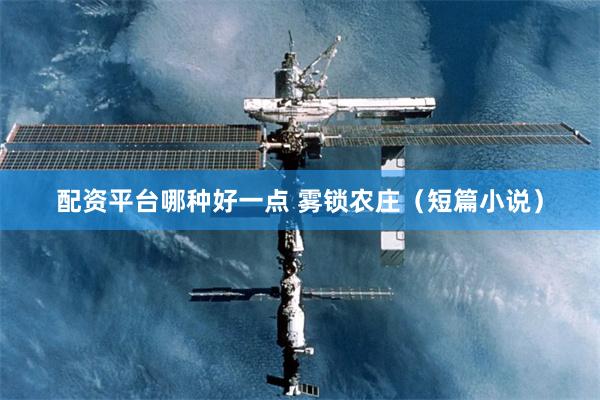
作者:吴树鸣
秦岭主峰太白山北麓的坡原延伸段上,终年弥漫着一层薄雾,斜岔口大队就匍匐在这片灰蒙蒙的天穹下,像被时光遗忘的疮疤。
这是个清末民初遗留下来的老庄子。一眼望去,破败不堪:路面坑坑洼洼,牛车过后便扬起漫天灰尘;小河旁堆满了农药袋和烂菜叶,空气中混杂着粪土与腐烂物的恶臭。庄户人们有着瘦弱的身影,衣衫褴褛,脸上颧骨高耸,眼神浑浊,仿佛早已习惯了生活的折磨。
举目望去,整个庄子全是土墙屋,不少屋顶上还覆盖着茅草。天刚蒙蒙亮,七十岁的老梁头就蹲在自家田埂上,一袋接一袋地抽着旱烟。他面前的四亩玉米地已经干裂出口子,像一张张渴极了的嘴巴。而相邻的地里,水渠正哗哗流淌。
“梁叔,还不浇地啊?再旱下去,这季玉米可就全完了。”卖菜回来的陈老四缩着脖子路过,压低声音说道。
老梁头浑浊的眼睛望着地里的裂缝,没搭话。他何尝不想浇地?可孙洋主任早就交代过水利员,谁家都能浇,就老梁家不行。
展开剩余80%孙洋是斜岔口的大队主任,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二十多年。
雾浓时,三五老人蜷缩在土墙根下晒太阳,如同雕塑般一动不动。十六岁的春妮背着比她还高的柴筐往家走,经过老秀才家门口时,停下脚步听了片刻——老秀才正在教几个娃娃认字。
“春妮,来听会儿不?”老秀才招呼道。春妮摇摇头,指了指背后的柴筐:“还得赶回去做饭哩。”
她认得三百来个字,原本去年有机会去人民公社街道读职高,可孙主任卡着贫困证明不给开,这事就黄了。在斜岔口,娃娃们没有玩具、没有网络,最大的娱乐就是过年时草台班子的破锣戏,平日里的乐趣不过是上树掏鸟窝、下河摸泥鳅。
老梁头家原本是有盼头的。他家四个儿子,老二最有出息,在省城学了技术,每个月能往家寄点钱。几年下来,老梁头翻修了屋顶,换了新农具,饭桌上偶尔能见点荤腥。
可就这点“富”,被是非头胡婆娘早看到了,她屁颠屁颠地去讨好孙洋,添盐加醋地渲染了一番。孙洋坐不住了,那表情里面分明写满了嫉妒。
“这是我孙家的一亩三分地,谁叫你们比我好啊?”有一回孙洋喝醉了,拍着老梁头的肩膀这么说,眼睛里的光让人发寒。
从此,老梁家就没过过安生日子。不是浇地被卡,就是盖房被拦。去年老梁家想盖间厢房,孙洋借职务之便,三番五次带公社土地办的人来工地找茬,停工通知下了一次又一次。最近小儿子想参军,孙洋又暗中作梗,政审就是过不了。
“这雾啊,锁的不是庄子,是人心。”老秀才常这么说。他是这个庄子最有文化,最有人缘的老者,他经常抬头看天,给人说“天晴了,雾还能不散吗?快看,不远了!”
他指的是孙洋上台前的光景。那时庄子穷是穷,可民风淳朴温良,家家户户虽然搜不出三斤余粮,但至少不会有人半夜翻墙拖人去结扎,不会浇地时突然被人掐断水源。
说起半夜结扎的事,庄里人都知道二柱家的遭遇。二柱有两个女儿,还想再生个儿子,那天在集体劳动时和孙洋吵了几句。当天半夜,孙洋带着计生办的人从后墙翻进二柱家,把哭喊着的二柱媳妇直接拖到公社医院做了绝育手术。
就这还不算完,后来二柱去大队开证明,孙洋吩咐手下人一律不给办。如今二柱媳妇整天呆呆傻傻的,见人就躲。
日头升高了些,雾稍微散去。老梁头终于站起身,拍了拍屁股上的土,朝家走去。路上遇见孙洋的两个狗腿子——苟剩和朱杆,二人正叼着烟卷,晃晃悠悠地巡查什么似的。
“梁叔,地浇上了吗?”苟剩故意问道,露出满口黄牙。老梁头没吭声,低着头继续走。 “听说你家老二在省城混得不赖啊,什么时候带咱们也去见识见识?”朱杆在后面喊道。
老梁头加快脚步,背后的笑声尖锐刺耳。
孙洋之所以能横行乡里二十多年,主要靠的是他媳妇的他舅的儿媳妇她爸,听说那个人在县上哪个单位当一把手好些年了;还有靠的就是拉帮结派。那些没立场的庄户人看他“势大”,就跟在他屁股后头转。有几个人简直成了专业狗腿子,站在孙洋角度,让咬谁就咬谁。再加上几个附和的,使本来就不知天高地厚的孙洋自我感觉更加了不起,似乎人生走到了“高光时刻”。
暮色再度合拢时,孙洋家的三层瓷砖小楼亮起灯火,麻将声吵吵嚷嚷传出院墙。院外蹲着几个等开证明的庄户人,一个个缩着脖子,不敢大声说话。
陈老四也来了,他攥着户口本,想给两个女儿开上学证明。孙家的狼狗突然狂吠起来,吓得他后退几步,跌坐在泥坑里。院里传出哄笑声,不知道是谁扔出来个空酒瓶,碎在陈老四脚边。
“明天再来吧,没看主任正忙打牌吗!”苟剩从门缝里探出头来,喷着酒气喊道。
陈老四爬起身,望着孙家明晃晃的灯光,突然对着浓雾嘶喊:“天啊!清明盛世到底啥时候来啊!”
雾更浓了,吞噬了叫喊声,吞噬了土屋里微弱的煤油灯光,吞噬了整个斜岔口大队。只有山风卷着粪土气息穿过茅草屋,像无数声压低的叹息,在秦岭北麓的坡原上久久不散。
那夜老梁头做了个梦,梦见老二带着县委的人来了,孙洋和他的狗腿子们被带上警车,庄户人们争相奔走相告......
第二天雾散得迟,老梁头还是蹲在地头。龟裂的土块硌着他豁口的旧鞋,远处孙家小楼的麻将声似乎响了一夜。他望着枯死的玉米苗,突然想起老二悄悄捎回来的话,说新来的县委书记最恨贪腐村霸。
太阳终于挣脱雾霭,第一缕阳光刺穿云层,照在老人攥紧的拳头上。土路上传来摩托车的声响,老梁头站起身,手搭凉棚望向远处——那是邮递员小张,车后座上坐着个干部模样的人,他手里拎着个公文包。
雾锁农庄的第三千二百四十七个清晨,或许真的会有些不同,老梁头觉得,眼前的雾在慢慢散开了。他拍拍身上的尘土,朝着摩托车的方向,一步步走去。
1995年春节于槐芽
发布于:陕西省